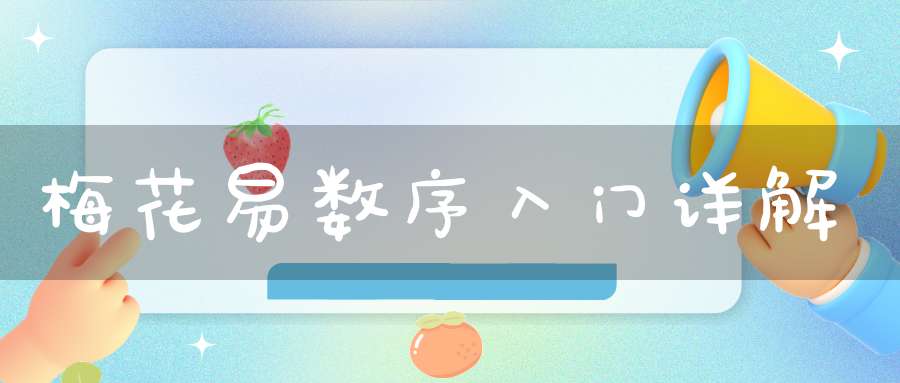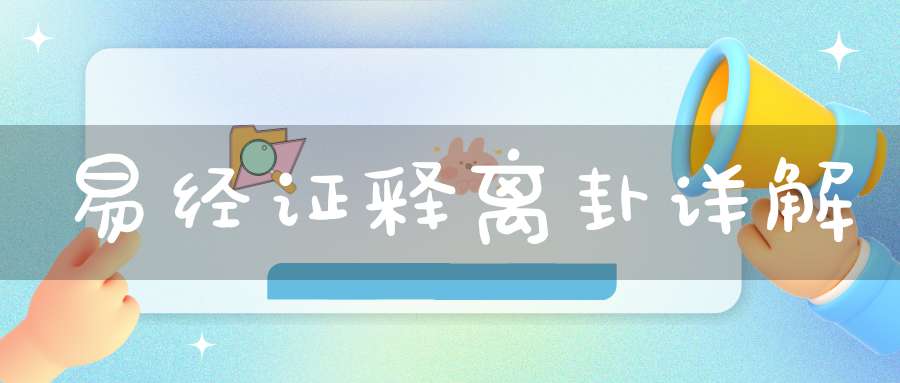抱朴子69章,外篇.知止注解在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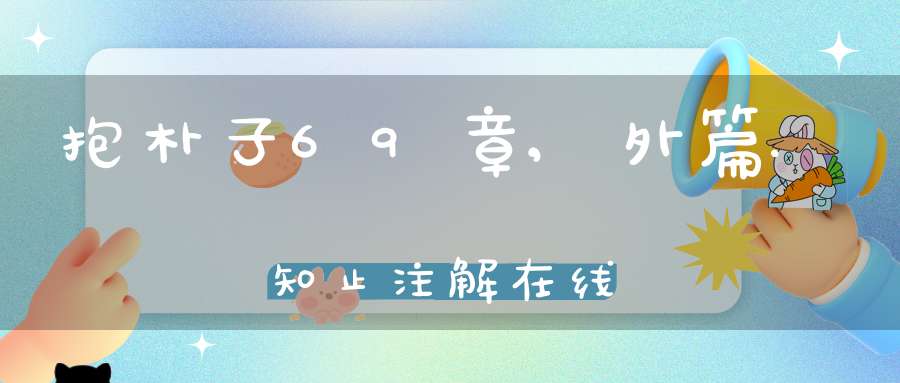
《抱朴子》69章 外篇.知止
抱朴子曰:祝莫大於无足, 福莫厚乎知止. 抱盈居冲者, 必全之算也;宴安盛满者, 难保之危也. 若夫善卷巢许管胡之徒, 咸蹈云物以高骛, 依龙凤以竦迹, 觇韬锋於香饵之中, 寤覆车乎来轫之路, 违险途以遐济, 故能免詹何之钓缗, 可谓善料微景於形外, 觌坚冰於未霜, 徙薪曲突於方炽之火, 纚舟弭楫於冲风之前, 瞻九牛害而深沈, 望密蔚而曾逝, 不托巢於苇苕之末, 不偃寝乎崩山之崖者也. 斯皆器大量弘, 审机识致, 凌侪独往, 不牵常欲, 神叁造化, 心遗万物, 可欲不能虿介其纯粹, 近理不能耗滑其清澄. 苟无若人之自然, 诚难企及乎绝轨也. 徒令知功成者身退, 处劳大者不赏, 狡兔死则知猎犬之不用, 高鸟尽则觉良弓之将弃. 鉴彭韩之明镜, 而念抽簪之术;睹越种之暗机, 则识金象之贵. 若范公泛艘以绝景, 薛生逊乱以全洁, 二疏投印於方盈, 田豫释绂於漏尽, 进脱亢悔之咎, 退无濡尾之吝, 清风足以扬千载之尘, 德音足以祛将来之惑. 方之陈宝, 不亦邈乎!
或智小败於谋大, 或辕弱折於载重, 或独是陷於众非, 或尽忠讦於兼会, 或倡高算而受晁错之祸, 或竭心力而遭吴起之害. 故有口止局高口止脊厚, 犹不免焉. 公旦之放, 仲尼之行, 贾生逊摈於下士, 子长熏肾乎无辜, 乐毅平齐, 伍员破楚, 白起以百胜拓疆, 文子以九术霸越, 韩信功盖於天下, 黥布灭家以佐命, 荣不移晷, 辱已及之. 不避其祸, 岂智者哉! 为臣不易, 岂将一途, 要而言之, 决在择主. 我不足赖, 其验如此. 告退避贤, 洁而且安, 美名厚实, 福莫大焉. 能修此术, 万未有一. 吉凶由人, 可勿思乎! 逆耳之言, 乐之者希, 献纳期荣, 将速身祸, 救诽谤其不暇, 何信受之可必哉!
夫矢曾缴纷纭则鸳雏徊翮, 坑阱充蹊则麟虞敛迹. 情不可极, 欲不可满, 达人以道制情, 以计遣欲, 为谋者犹宜使忠, 况自为策而不详哉! 盖知足者常足也, 不知足者无足也. 常足者, 福之所赴也;无足者, 祸之所锺也. 生生之厚, 杀哉生矣, 宋氏引苗, 郢人张革, 诚欲其快, 而实速萎裂, 知进忘退, 斯之谓乎?
夫筴奔而不止者, 鲜不倾坠;凌波而无休者, 希不沈溺;弄刃不息者, 伤刺之由也;斫击不辍者, 缺毁之原也. 盈则有损, 自然之理, 周miao之器, 岂欺我哉? 故养由之射, 行人识以驰弦, 东野之御, 颜子知其方败, 成功之下, 未易久处也. 夫饮酒者不必尽乱, 而乱者多焉;富贵者岂其皆危, 而危者有焉. 智者料事於倚伏之表, 伐木於毫末之初, 吐高言不於累棋之际, 议治裘不於群狐之中, 古人佯狂为愚, 岂所乐哉! 时之宜然, 不获已也. 亦有深逃而陆遭波涛, 幽遁而水被焚烧, 若龚胜之绝粒以殒命, 李业煎蹙以吞鸩, 由乎迹之有朕, 景之不灭也. 若使行如蹈冰, 身如居阴, 动无遗踪可寻, 静与无为为一, 岂有斯患乎! 又况乎揭日月以隐形骸, 击建鼓以徇利器者哉! 夫值明时则优於济四海, 遇险世则劣於保一身, 为此永慨, 非一士也.
吾闻无炽不灭, 靡溢不损, 焕赫有委灰之兆, 春草为秋瘁之端, 日中则昃, 月盈则蚀, 四时之序, 成功者退. 远取诸物, 则构高崇峻之无限, 则颓坏惟忧矣;近取诸身, 则嘉膳旨酒之不节, 则结疾伤性矣. 况乎其高概云霄而积之犹不止, 其威震人主而加崇, 又不息者乎! 蚊虻堕山, 适足翱翔;兕虎之坠, 碎而为齑. 此言大物, 不可失所也. 且夫正色弹违, 直道而行, 打扑干纪, 不虑雠隟, 则怨深恨积. 若舍法容非, 属托如响, 吐刚茹柔, 委曲绳墨, 则忠□丧败, 居此地者, 不变劳乎? 是以身名并全者甚希, 而折足覆食束者不乏也. 然而入则兰房窈窕, 朱帷组帐, 文茵兼舒於华第, 艳容粲烂於左右, 轻体柔声, 清歌妙舞, 宋蔡之巧, 阳阿之妍, 口吐辨菱延露之曲, 足蹑渌水七槃之节, 知音悦耳, 冶姿娱心, 密宴继集, 醽醁不撤, 仰登绮阁, 俯映清渊, 游果林之丹翠, 戏蕙囿之芬馥, 文鳞瀺灂, 朱习颉颃, 飞缴堕云鸿, 沈纶引鲂鲤, 远珍不索而交集, 玩弄纷华而自至. 出则朱轮耀路, 高盖接轸, 丹旗云蔚, 麾节翕赫, 金口嘈口献, 戈甲璀错, 得意托於後乘, 嘉旨盈乎属车, 穷游观之娱, 极畋渔之欢. 圣明之誉, 满耳而入;谄悦之言, 异口同辞. 於时眇然, 意蔑古人, 谓伊吕管晏, 不足算也.
岂觉崇替之相为首尾, 哀乐之相为朝暮, 肯谢贵盛, 乞骸骨, 背朱门而反丘园哉! 若乃圣明在上, 大贤赞事, 百揆非我则不叙, 兆民非我则不济, 高而不以危为忧, 满而不以溢为虑者, 所不论也. 穷达
或问:“一流之才, 而或穷或达, 其故何也? 俊逸絷滞, 其有憾乎? ” 抱朴子答曰:“夫器业不异, 而有抑有扬者, 无知己也. 故否泰时也, 通塞命也. 审时者何怨於沈潜, 知命者何恨於卑瘁乎! 故沈闾渟钧, 精劲之良也, 而不以击, 则朝菌不能断焉;珧华黎绿, 连城之宝也, 委之泥泞, 则瓦砾积其上焉. 故可珍而不必见珍也, 可用而不必见用也. 庸俗之夫, 暗於别物, 不分朱紫, 不辩菽麦, 唯以达者为贤, 而不知侥求者之所达也;唯以穷者为劣, 而不详守道者之所穷也. 且夫悬象不丽天, 则不能扬大明灼无外, 嵩岱不托地, 则不能竦峻极概云霄. 兔足因夷途以聘迅, 龙艘泛激流以效速, 离光非燧人不炽, 楚金非欧冶不剡, 丰华俟发春而表艳, 栖鸿待冲飙而轻戾, 四岳不明扬, 则有鳏不登庸, 叔牙不推贤, 则夷吾不式厚, 穰苴赖平仲以超踔, 淮阴因萧公以鹰扬, 隽生由胜之之谈, 曲逆缘无知之荐, 元直起龙萦之孔明, 公瑾贡虎卧之兴霸, 故能美名垂於帝籍, 弘勋著於当世也.
“汉之末年, 吴之季世, 则不然焉. 举士也, 必附己者为前;取人也, 必多党者为决;而附己者不必足进之器也, 同乎我, 故不能遗焉;而多党者不必逸群之才也, 信众口, 故谓其可焉. 或信此之庸猥, 而不能遣所念之近情;或识彼之英异, 而不能平心於至公. 於是释铨衡, 而以疏数为轻重矣;弃度量, 而以纶集为多少矣. 於时之所谓雅人高韵, 秉国之钧, 黜陟决己, 褒贬由口者, 鲜哉免乎斯累也. 又况於胸中率有憎独立, 疾非党, 忌胜己, 忽寒素者乎? 悲夫! 邈俗之士, 不群之人, 所以比肩不遇, 不可胜计, 或抑顿於薮泽, 或立朝而斥退也.
盖修德而道不行, 藏器而时不会, 或俟河清而齿已没, 或竭忠勤而不见知, 远行不骋於一世, 勋泽不加於生民. 席上之珍, 郁於泥泞, 济物之才, 终於无施, 操筑而不值武丁, 抱竿而不遇西伯, 自曩迄今, 将有何限? 而独悲之, 不亦陋哉! 瞻径路之远, 而耻由之;知大道之否, 而不改之. 齐通塞於一途, 付荣辱於自然者, 岂怀悒闷於知希, 兴永叹於川逝乎! 疑其有憾, 是未识至人之用心也. 小年之不知大年, 井蛙之不晓沧海, 自有来矣. 重言
抱朴子曰:余友人玄泊先生者, 齿在志学, 固已穷览六略, 旁综河洛, 昼竞羲和之末景, 夕照望舒之余辉, 道靡远而不究, 言无微而不测, 以儒墨为城池, 以机神为干戈, 故谈者莫不望尘而衔璧, 文士寅目而格笔. 俄而寤智者之不言, 觉寸一之无咎, 意得则齐荃蹄之可弃, 道乖则觉唱高而和寡, 於是奉老氏多败之戒, 思金人三缄之义, 括锋颖而如讷韬, 修翰於彤管, 含金怀玉, 抑谧华辩, 终日弥夕, 或无一言.
门人进曰:“先生默然, 小子胡述? 且与庸夫无殊焉. 窃谓锺不鸣, 则不异於积铜;浮磬息音, 则未别乎聚石也.” 玄泊先生答曰:“吾特收远名於万代, 求知己於将来, 岂能竞见知於今日, 标格於一时乎? 陶甄以盛酒, 虽美不见酣;身卑而言高, 虽是不见信. 徒卷舌而竭声, 将何救於流遁? 古人六十笑五十九, 不远迷复, 乃觉有以也. 夫玉之坚也, 金之刚也, 冰之冷也, 火之热也, 岂须自言, 然後明哉! 且八音九奏, 不能无长短之病, 养由百发不能止, 将有一失之疏, 玩凭河者, 数溺於水;好剧谈者, 多漏於口. 伯牙谨於操弦, 故终无烦手之累;儒者敬其辞令, 故终无枢机之辱. 浅近之徒, 则不然焉. 辩虚无之不急, 争细事以费言, 论广修坚白无用之说, 诵诸子非圣过正之书, 损教益惑, 谓之深远, 委弃正经, 竞治邪学. 或与暗见者较唇吻之胜负, 为不识者吐清商之谈对, 非敌力之人, 旁无赏解之客, 何异奏雅乐於木梗之侧, 陈玄黄於土偶之前哉! 徒口枯气乏, 椎杭抵掌, 斤斧缺坏而盘节不破, 勃然战色而乖忤愈远, 致令恚容表颜, 丑言自口, 偷薄之变, 生乎其间, 既玷之谬, 不可救磨. 未若希声不全大音, 约说以俟识者矣.
庄子经典
抱朴子外篇讲什么?
外篇》的基本内容 《外篇》言人事,以儒家为宗,反映了葛洪先儒后道的思想发展轨迹。 《弭讼》等9篇论述时政得失,讥刺世俗,言治民之法。 《臣节》等7篇评人事臧否,主张藏器待时,克己思君。 《君道》等14篇谏君主任贤举能,爱民节欲,独掌权柄。 《勖学》、《崇教》两篇论超俗出世。 《交际》等5篇论修身。 《钧世》等7篇论文言著书之贵。 《诘鲍》篇主张有君。 《博喻》、《广譬》两篇皆替喻,重复诸篇思想。 《自叙》一篇殿后,乃自传体,亦为全书之序。 《外篇》论时政得失,托古刺今,讥评世俗,述治民之道,主张任贤举能,爱民节欲。《四库提要》谓其“辞旨辨博,饶有名理。”鲁迅赞其“论及晋末社会状态”。 《外篇》还阐述了进步的文学观,强调要注重思想内容和社会作用,主张立言必须有助于教化,同时提倡文章与德行并重。认为文学是发展的,今胜于古,既要反对唯古是尊,又要反对厚今薄古。强调文学批评要注意作者的风格、个性,要广录博收,反对偏嗜和浅尝。 葛洪在《抱朴子》一书之中,将玄学与道教纳为一体,将神学与道学纳为一体,将方术与金丹纳为一体,将丹鼎与符炁纳为一体,将儒学与仙学纳为一体,从而确立了道教的神仙理论体系。
葛洪《抱朴子·外篇》卷14用刑诗解3罚贵得罪罚重其轻
葛洪《抱朴子·外篇》卷14用刑诗解3罚贵得罪罚重其轻
题文诗:
国非无令, 国亡 患于,令烦不行;军非无禁,
军败 患于,禁设不止.众慝弥蔓,下黩其上.
赏贵当功,而不必重,罚贵得罪,而不必酷.
鞭废于家,僮仆怠惰; 刑 息于国,群下不虔.
爱 必 待敬,不 衰 败故,制礼崇之;德须威而,
能 久立故,作刑肃之. 鲁 班 工 倕,不委规矩,
故 能 方圆,不戾于物;明君 义正, 不释法度,
故机诈 人, 不肆其巧.唐 尧 虞 舜, 其仁如天,
不原四罪;姬公 旦也, 友于兄弟,不赦二叔.
孔 仲尼之,诛 少 正卯;汉武 帝 之,杀 其 外甥,
垂泪惜法,盖不 得 已.诛一振万,损少成多.
方之栉发,所利者众;比于割疽,所全者大.
灸刺惨痛,而不可止,以痊病也;刑法凶丑,
而不可罢,以救弊也.六军如林,未必皆勇,
排锋陷火,人情所惮.恬颜劝之,投命者尠 ?;
断斩威之,莫不奋击.役欢笑者,不及叱咤;
诱悦未若,刑戮之齐. 鞅 疾弃灰,而峻其辟.
以其所畏,禁其所玩,峻而不犯,全民之术.
明治病术,杜未生疾;达治乱要,遏将来患.
若以轻刑,禁重罪 者,若 以薄法, 以 卫厚利,
陈之滋章,犯者弥多,穿阱当路,仁人非用.
【原文】 亡国非无令也,患于令烦而不行;败军非无禁也,患于禁设而不止。故众慝弥蔓,而下黩其上。夫赏贵当功而不必重,罚贵得得罪而不必酷也。鞭朴废于家,则僮仆怠惰;征伐息于国,则群下不虔。爱待敬而不败,故制礼以崇之;德须威而久立,故作刑以肃之。班倕不委规矩,故方圆不戾于物;明君不释法度,故机诈不肆其巧。唐虞其仁如天,而不原四罪;姬公友于兄弟,而不赦二叔。仲尼之诛正卯,汉武之杀外甥,垂泪惜法,盖不获已也。
【译文】国家灭亡并非因为没有法令,坏事就坏在法令烦琐并且不实行;军队打败仗并非因为没有禁令,坏事就坏在禁令虽设而不起作用。因此众多的邪恶蔓延,臣下轻慢君王。赏赐,重要之处在于符合功劳,但不必重;惩罚,可贵之处在于罪有应当,但不必严酷。在家里,鞭打责罚如果不用了,奴仆就懈怠懒惰;在国家,法律制裁如果停止了,众多下民就会不敬爱主上。爱,需要尊敬才能不衰败,所以要制定礼,以便让人们崇尚它;德,必得威权方会长远确立,所以要制定刑,以便让人们恭敬它。鲁班、工倕不扔开圆规方矩,所以制做的东西都不离方圆;贤明的君主不放弃法度,所以狡诈的人不能任意虚巧。
【原文】 唐、虞其仁如天,而不原四罪;姬公友于兄弟,而不赦二叔。仲尼之诛正卯,汉武之杀外甥,垂泪惜法,盖不获已也。故诛一以振万,损少以成多。方之栉发,则所利者众;比于割疽,则所全者大。是以灸刺惨痛,而不可止者,以痊病也;刑法凶丑,而不可罢者,以救弊也。六军如林,未必皆勇,排锋陷火,人情所惮。然恬颜以劝之,则投命者 尠? ;断斩以威之,则莫不奋击。故役欢笑者,不及叱咤之速;用诱悦者,未若刑戮之齐。
【译文】唐尧、虞舜的仁义像天一样广阔,但并不原谅共工等四个罪人;周公与兄弟友善,但并不赦免管叔和蔡叔。孔仲尼杀少正卯,汉武帝杀外甥,都是流着眼泪但又顾惜法律,不得已而为啊。所以杀一个人但挽救一万人,损害了少数人但成全了多数人。用篦头发来打比方,掉几根头发,但对多数头发有利;用割痈疽来作比喻,去掉了毒疮,所保全的是整个身体。因此,艾灸针刺虽然疼得很厉害,但也不能抛开不用,为的是治好疾病;施刑执法虽然凶狠难看,但也不能作罢,为的是解除弊端。六军的兵将像树林一样,未必都勇敢,排开利刃冲入火海,害怕是人之常情。但以平静的表情去鼓励人们,舍命的人很少;用斩杀的办法来威吓,就没有人不奋力进击。因此用让人高高兴兴的办法,不如大声喝斥迅速;用让人愉快的诱导的办法,不如刑罚杀戮来得整齐划一。
【原文】 是以安于感深谷而严其法,卫子疾弃灰而峻其辟。夫以其所畏,禁其所玩,峻而不犯,全民之术也。明治病之术者,杜未生之疾;达治乱之要者,遏将来之患。若乃以轻刑禁重罪,以薄法卫厚利,陈之滋章,而犯者弥多,有似穿阱以当路,非仁人之用怀也。
【译文】因此董安于受到深谷的启发而严厉其刑法,商鞅痛恨把灰烬丢弃于路而峻整其律条。用人们所畏俱的来禁止人们所轻忽的,严厉而使人不敢侵犯,是保全人民的办法。明了治病方法的人,要在生病之前预先杜绝;通达治理混乱要旨的人,要在祸患到来前就去阻遏。至于说以轻的刑罚禁绝重罪,以薄的法律卫护厚利,那么就会越是陈述得清楚,违犯者也越多,就像在道路上凿陷井等于害人一样,不是仁德的人应有想法。
关于《抱朴子》和东密教的问题.
“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九字,典出抱朴子内篇第四登涉篇, 又称“六甲秘祝”,(长空注:用于咒语则是日本真言宗的首创),有人说有“在”:“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行”称十字大禁咒,无则称九字大禁咒,不知据何而言. 特别是“十字大禁咒”一辞似乎不见于经典,一般皆称“九字”或“九字印”. 至于九字是哪九字,在后魏昙鸾的往生论注卷下另载:“....但一切齿中诵临兵斗者皆陈列在前行诵此九字五兵之所不中抱朴子谓之要道者也....”将“阵列前行”引成了“陈列在前行”, 阵陈可通, 而“在”字应是衍文 (不小心多抄的字) , 所以还是九字, 不该有十字才对. 抱朴子提出九字的目的是讲入山求仙修道时的护身之术(登涉整篇都在解释这些) ,以咒文护身,,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 咒文都是祭祀用的,只有掌祭的巫祝才懂; 佛教传入中国后带来很多真言 (陀罗尼) ,影响到当时也刚开始发展的道教, 才渐渐有各种咒文的出现,像“急急如律令”一词, 就是汉朝公文用语, 被道教用作咒文的结语形式. 看“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这种句法, 绝不可能出现于汉朝之前, 有人说它和“乾元亨利贞”一样古老, 很有问题。
从抱朴子书中看来, 咒文的使用方式是反覆祝诵某个具神秘力量的存在 (日月, 星辰, 天地....等等) , 祈求灵力的赐予, 使念咒者也得到非凡的神秘力量, 这也是因为古代中国并没有那种冥想以精神力决胜负的方式 (儒家敬天, 讲天人相应, 道家讲与道冥合, 都是很高的精神境界,
但是都不是宗教, 追求神秘的力量以超越人有限的存在, 不是儒家和道家之所为) . 以九字而言, 不管是配上九个手印或是用纵横法 (在空中画五横四纵, 一字一画) , 都是要借外力以行法术, 并非是以冥想的方式提高自己的精神力量.
由此可以理解为东寺流(东密)本来就是鉴真从唐朝传到日本的密宗分支,其中夹杂了少许的道教思想也不足为怪,而正是这些道教神秘色彩的内容正好符合忍者的特点,所以才被剽窃了。
正如武田信玄剽窃孙子兵法的风林火山一样
不过在日本也另有一说
话说大约在公元1030年前后,源氏同平氏打仗,平氏战败(后有小说《源氏物 语》及《平家物语》),小主人由七位武士护送要逃到北方,仇家各处设置关卡,捉拿平家少主。
一行九人来到最后一个关卡,关防主管是个佛教徒,副官原先曾见过平家主人,认得少主面 孔,八人最后无法可想,领头的将军提议,就由少主扮作苦力,和另一个苦力头戴斗笠一同在 后,七武士项挂佛珠,手拿禅杖,扮作和尚说是要到北方化缘。
主管一看七人身穿战甲,腰佩武士刀,横看竖看都不像和尚,就问说你既然要化缘,可有贵 寺的化缘公告,七人一阵紧张,将军由行李抽出一空白卷轴,对着空白轴里,临时自编、高声诵 赞布施功德。由於他一字一字用很慢的声调唱出( 一面要编内容嘛 ),关防副官就偷偷要走到后面 看一看到底有没有字,将军刚好念完,对副官大吼一声「阿弥陀佛保佑你」,副官吓一跳,退而 作罢,将军就趁势收好卷轴。
主管又问,既是和尚为何有刀有甲,答各宗不同,本宗以剑为智,以甲为悲, 仗为方便, 佛珠为究竟。主管又问,所宗者何? 答法主本尊不动明王(因为他右手中拿剑),法王西方阿弥陀佛 (刚刚用来吓退副官)。
主管也是佛教徒,当然也就问他既是不动明王为本尊,那请问可有咒语? 这一来将军也楞了, 怎麽办,临机一动,於是回答当有九字真言,为不动明王密咒。於是当兵打仗的那一套,在平剧 该唱:「一字排开来长蛇一(啊)阵」,将军回答的是日式的文法:「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一面说一面以左手捧右手剑指,随手在空中划个方形网状(不动明王左手拿的是绢索)。
所以这也算是“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的一种来历。
附文:道教与密宗的联系
一、道教是否影响了密宗
密宗的出现是印度佛教发展史上一件非常重要且引起众多争议的大事,其争议之处主要表现为密宗将人之性爱引入了佛教的教义和宗教实践之中。早期佛教学说与性爱本来是水火不相容的,现在,密宗却不仅承认了性行为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而且进一步将人的性行为赋予了崇高而神圣的意义,性行为和性象征在密宗的修行仪式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佛教的教法和修习实践因此经历了一场相当巨大的变化。公元8世纪时,密宗已成为印度佛教发展中的主流。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按印度学者的看法,印度密宗(注:印度密宗有所谓佛教密宗和印度教密宗之分。前者主要指金刚乘或真言宗,后者主要指性力派,二者之间相互影响,一般来说,是佛教密宗出现在先,所以在此主要讨论密宗。)的出现,并不是当时印度正统文化的继续。德?恰托巴底亚耶说,尽管密宗也像“吠陀”一样有其咒术和仪式,“但很清楚密教是反吠陀的,起码在它的早期阶段是反对吠陀传统的”(60)。(注:参阅德?恰托巴底亚耶:《顺世论》,王世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400。)恰托巴底亚耶采纳印度和西方学者较为一致的看法,认为中国的道教对印度密宗的出现起到了外部影响的作用。公元7世纪时,印度已开始从事《道德经》的梵文翻译,这主要集中在印度东部的阿萨姆地区。再者,“中国”(即“支那”)在印度密宗文献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条证据首先是由巴克奇提出的:“有一种称为支那行(cinacara)的修行法,学者们已经讨论得很多了。为印度教和佛教两方面都采纳了的《秘密地母经》说到支那地母(Cina Tara)的崇拜来自于大支那国家(即中国)。据说婆喜史多,最伟大的婆罗门圣者之一,曾去那个国家会晤佛陀,那个时候在印度或西藏是找不到佛陀的,婆喜史多(Vasistha)在那里接受佛陀的灌顶,学到支那行的秘密教义,后来回到印度宏扬此教”(转引自德?恰托巴底亚耶414)。但恰托巴底亚耶认为,尽管印度密宗中有外来成份,但密宗的出现与印度古老的非正统的民间文化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密教非常古老;有些权威学者猜想它比吠陀还要古老。数论和密教的基本范畴是阴(prakriti)和阳(purusa)。再者在数论和密教看来,至少就宇宙发展过程而论阴是基本的主要的”(转引自德?恰托巴底亚耶60)。所以,在恰托巴底亚看来,印度的密宗对阴性文化的强调并不是追随了道教,而是其本身固有的性质使其如此,换言之,印度密宗天然存在着吸收道教成份的民间文化基础。所以,密宗的出现是佛教在印度通俗化普及化的结果:一方面它是佛教的通俗化,另一方面它又是印度原始密教的崇高化。
我国也有学者认为,印度佛教中的密宗,既不是来自印度教或是印度更为古老的民间文化传统,也不是来自佛教,而是来自道教。汶江认为,印度古代的迦摩缕波不仅很早就和中国有直接而频繁的交往,而且也是密宗的滥觞之地。他用以印证自己观点的材料主要有以下几则:
一,《旧唐书?天竺传》:“天竺所属国数十,风俗略同,有迦没路国(即迦摩缕波),其俗开东门以向日,王玄策至,其王发使,贡以珍奇异物及地图,因请老子像及道德经。”
二,《新唐书》卷二二一上:“东天竺王尸鸠摩(即《大唐西域记》中的拘摩罗),送牛马三万馈军,及弓刀宝缨络,迦没路国献异物,并上地图请老子像。”
三,关于翻译《道德经》为梵文的事,《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贞观廿一年,西域使李义表还奏称,东天竺童子王所未有佛法,外道宗盛,臣已告云:‘支那大国未有佛法以前,旧有圣人说经,在俗流布,但此文不来,若得闻者,必当信奉。’彼王言:‘卿还本国,译为梵言,我欲见之,必道越此徒,传通不绝。’登即下敕,令玄奘与诸道士共译出,于时道士蔡晃、成英二人,李宗之望,自余锋颖三十余人,共集五通观,同别参议,详校《道德》。奘乃句句披析,穷其义类,得其旨理,方为译之”(汶江119-120)。
陈寅恪在《〈大乘义章〉书后》一文中谈到“道”字的译法时,也引征了《集古今佛道论衡》中的资料:唐代初年,印度方面想得到《道德经》的梵文译本,玄奘奉敕,精心琢磨,将至关重要的“道”字译为梵文“末伽”,但与玄奘一起工作的道士则不以为然,执意认为应译为“菩提”(陈寅恪2)。在此之前,老子之“道”到底应译为“末伽”还是“菩提”已有争论,这说明《道德经》的关键词语翻译成梵文该当如何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了,所以陈寅恪在谈论晋代的《大乘义章》时连带着谈论到《道德经》的翻译问题。当然,起初这个问题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佛教传入中国时,要依附于老庄之“道”,但后来当老庄之“道”传入印度时,难免也要依附于佛教,所以道士们宁可将道家之“道”译成佛教中的“菩提”。
季羡林说:“我们讲‘文化交流’,其中‘交’字是关键。既然说‘交’,就不会是向一个方向流,形成了所谓one-way traffic,而是相向地流,这才是真正的‘交流’。 ……有时候,流过来的东西,经过这一方的改造、加工、发展、提高,又流了回去。……这种流出去又流回来的现象,我称之为‘倒流’。……佛教是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在佛教义理方面,中国高僧在几百年上千年的钻研与学习中,有了很多新的发展,有的又‘倒流’回印度,形成了我所说的‘佛教的倒流’”(季羡林184-185)。
我们知道,佛教初入中国时,多依托与之相近的道家的说法,以期得到理解,所以道释很快就合流了,及至佛教再倒流回印度时,老庄思想也随之传播过去了。与季先生“佛教倒流”说相应,李约瑟认为,道教的性理论和实践盛行于中国是在公元2至6世纪,这是在印度的密教崇拜兴起之前。所以,初看起来,密教似乎是从印度输入到中国,但实际的情形是,先是道教从中国输入印度,然后才是密教回头又输入中国。所以,这也是一种回头输入的情况,“很可能密教是外国殷勤教授中国人他们本来已经很熟悉的东西的又一例证”(转引自德?恰托巴底亚耶415)。
二、道教是如何影响密宗的
从以上的材料中可以推断出,老子及其《道德经》在印度是早有所闻,或许在公元7、8世纪时《道德经》确实已翻译成了梵语,但这一切和印度佛教中密宗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关联?换句话说,道教在哪些方面对印度密宗的形成产生了作用?
按李约瑟在《中国科学与文化》中的看法,道教与印度密宗之间的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中国道教的宇宙起源论的确很类似于印度的密教;其二,道教和密教一样,有一种明显的偏于女性观点的倾向:将阴性观点和阴性法则置于阳性之上。李约瑟说:“由于普遍接受阴阳理论,十分自然地会对照宇宙的背景设想人的性行为与整个宇宙的机制的确具有很密切的关系。道教徒认为性欲绝非达到神仙地位的障碍(仙人=真人,为道教描述长生状态的用语),在许多重要方面还可以使它作为成为神仙的助力”(转引自德?恰托巴底亚耶407-411)。
因为古代印度不像古代中国那样注重历史,所以要在印度文献找到确切的史料来印证道教对密宗的影响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学者们多从道教与密宗的相似性上来分析二者之间的联系,但这些联系又常常是模糊不清的。
即以人体与宇宙之间的关系说起。密宗强调人的身体与宇宙自然之间的同化关系,认为人体是宇宙的缩影,人要认识宇宙,首先要认识人的身体,宇宙的一切都存在于人的身体之中。其显明的推论有二条。第一,如果我们能够了解人体的奥秘,也就有可能了解自然的奥秘。第二,宇宙的诞生并不比人的诞生更神秘。按照密经所说,宇宙是由色欲创造的,世界起源于阴阳之间的交合。就人而言,导致新生命创造的过程是男女结合,宇宙也是以同样的方式通过阴阳交合创造出来的。一般都认为,密宗和道教在宇宙观上是非常相似的,二者都是从人体和男女的结合上谈论宇宙和宇宙的生成。但正如笔者在上文论述的那样,这些看法并不能构成密宗和道教的理论特色,吠陀颂诗和奥义书中也有类似的看法。我们很难确定密宗宇宙观的来源就是道教。
再比如,密教和道教一样,有一种明显的偏于女性观点的倾向,将阴性法则置于阳性法则之上,只不过在道教中,这种阴性法则主要表现为玄之又玄的“道”,而在密宗中,这种阴性法则却具体化为女神。密宗是从大乘佛教中发展而来,但在大乘佛教的早期经文中,却没有女神,女神的出现是密宗不同于早期佛教的一个重要标志。密宗最重要的女神是多罗菩萨或多罗子(Taras)(注:即度母,救度之母,意为“能使人渡转世江河之母”,其本意为“极目精”或“眼瞳”。),在金刚乘中她是佛陀和菩萨的配偶,对于她的崇拜,在公元7世纪时已较为普遍。(注:参阅罗伯尔?萨耶:《印度—西藏的佛教密宗》,耿升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40。)印度一直有崇拜母亲女神的传统,但从远古哈拉巴文化至笈多王朝时代,女神崇拜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只是在密宗兴起之后,佛教的密宗与印度教的性力派相互作用、相互推动,才使女神崇拜在印度文化中占据了真正重要的地位。笈多王朝时期,神的女性配偶已经开始出现于印度神庙之中,之前,她们虽也存在,但多表现为影子般的形象。密宗中确实存在着女性的崇拜,但是,在德?恰托巴底亚耶等学者看来,密宗在这方面的倾向与印度古老的母系社会的习俗有着更多的联系,因此也不能认为,密宗对于阴性原则的强调就来源于中国的道教。
道教对印度密宗的出现和发展到底产生了什么具体而独特的影响呢?为什么当时的印度对老子及其《道德经》会产生浓厚的兴趣呢?
学者们在谈到印度密宗与道教的关系时,一般都要说到“支那行”(cinacara)这个梵文词语。正如上文巴克奇所指出的那样,印度密宗中有一种修习方式称作“支那行”,其意是中国方式的性爱仪式,但“支那行”是怎么来的?它具体指代的是什么?它与老子及其《道德经》又有什么关联呢?学者们对这些问题要么是含糊不清,要么是避而不谈。而事实上理解“支那行”的问题对解开印度密宗与道教之间的关系之谜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古代的房事养生,滥觞于《道德经》中的一段著名的话:“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转引自陈鼓应279)。老子从对婴儿的观察发现,养生长寿的根本在于节欲保精,这一看法至关重要,中国后来的房事养生学,无论是医家、道家还是儒家都以老子惜精爱气的说法为宗旨。先秦两汉时期以节欲保精为主,魏晋直至隋唐五代时期的房中学著作则强调还精补脑之说,以固精纵欲为特点。
从历史上看,魏晋至隋唐五代,不仅是佛教从印度东传到中国而且也是道教西传到印度并对印度密宗产生影响的时期,所以,如果说有什么“支那行”的话,当以“还精补脑、固精纵欲”为其特点。中国古代的房事养生本来并不限于道家,而是封建社会上层普遍流行的思想和观念,但人们谈论房事养生时却常常依托于道家,它似乎是道家的专门“功夫”;而道家谈论房事养生时,往往又要将它追溯到老子那里,比如南朝陶弘景(456-536)《御女损益》篇就明确地说:“老子曰:还精补脑,可得不老矣”(宋书功209)。中国古人尚且如此,也难怪当时的印度对《道德经》痴迷有加。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支那行”在印度的出现与老子《道德经》的梵语翻译问题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我们再看密宗是如何接受“支那行”的。密宗尽管千奇百怪,但修习者都要特别珍惜精液,密宗认为泄精不仅是一种罪过,而且使人走向死亡。为了保精、固精,密宗把性交作为一种修行方式,认为佛性隐藏在女性的阴户之中,但是与我们一般的印象颇为不同的是,性交作为一种修习行为,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泄精,相反却是为了抑制精液外泄。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首先它通过交媾的方式唤醒人身上的性力(贡达力尼,意为蛇,所以性力也可以叫作蛇力),然后通过瑜伽修行似的功力和技能使精液沿着脊椎上行到坐落于脑部的“千瓣莲花结”(Sahasrara)中,使精液与之交合为一体,从而获得崇高的解脱和智慧。显然,密宗的这种修习实践是中国房事养生学中所谓的“黄河倒流”、“固精纵欲”、“还精补脑”之说的印度翻版。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对印度《欲经》的考察中得到反证。《欲经》是古代印度关于性爱科学的经典之作,虽然其创作的年代并不确定,但它是在印度密宗兴起之前就已广泛流行当无疑问。作为一部性学经典,《欲经》对古代印度的各种性欲观和性爱习俗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考察与研究,但通观全书,找不到任何地方提及类似于印度密宗的性爱方式,也没有任何地方将性交与宗教性的修行混为一谈。
性与印度宗教尤其是原始佛教本来是相互排斥的,但通过密宗以及印度教中的性力派,二者却合为了一体。
三、身谛与艳欲主义
印度密宗,包括佛教和印度教的密宗,在印度的兴盛主要是公元7至10世纪,随着伊斯兰教对印度的入侵,密宗便在印度逐步走向了衰落,成为印度社会文化发展中的暗流。时间上与此大致相当,中国的房事养生学发展到宋代,由于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桎梏,房中之书不再像隋唐时期普遍地流传于士大夫之中,房事养生之术虽然也在一些道士中间流传,但已不可能有什么新的发展。
谈起中国的房事养生,多是“缙绅先生难言之”;说起印度的密宗,一般也都认为是佛教在印度的极大堕落。道家的房事养生理论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比较有限,而密宗对印度文化的影响却是不可估量的,这是因为印度密教的兴起和发展在印度是一种泛印度教化的现象,它影响了印度本土的所有宗教如印度教、耆那教等等,所以,密教的兴起不仅是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也是印度社会文化发展史的一件大事,不了解它,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无法理解印度文化。
马克思说,印度既是一个“淫乐世界”,又是一个“悲苦世界”,这在其宗教的古老传统里早就体现出来了:“这个宗教既是纵欲享乐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宗教;既是林伽崇拜的宗教,又是札格纳特的宗教;既是和尚的宗教,又是舞女的宗教”(马克思62-63)。学者们对这种奇特的现象进行了各种分析,但却较少认识到中国的道教在其中所产生的作用。笔者认为,各种宗教一般都是重灵魂而轻肉体的,而道家的房事养生学却使印度的密宗对人的身体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形成身谛(deha tattva,有关人的身体的真理)的说法。从这个角度来说,密教是一种极端形式的唯身观。
印度古代佛教曾经极力排斥性行为,将人的性欲视若魔鬼,必须将它从僧侣们的生活中排除出去。因此,佛教僧侣们习惯将身体视为由鲜血、各种体液、粪便和骷髅组成的一整套令人厌恶的整体,将来必会解体,这正如早期佛教经典《经集》所说:“身体由骨和腱连接而成,粘上膜和肉,裹上皮,这样,身体的真相就看不见了。身体里装满肠、胃、肝、心、肺、肾和脾。还有鼻涕、唾液、浆液、润滑液、胆汁和脂肪。从它的七窍中,经常有污秽流出,眼屎从眼中流出,耳屎从耳中流出,有时吐出痰,汗液从身体排出。它的头颅充满窟窿,里面装着脑子。傻瓜出于无知,才认为它是好东西”(《经集》27)。
而密宗则将身体看得非常重要,将人的身体比作一只可以渡过苦海的船只,是众生借以解脱的根本依托。(注:参阅宋书功编著:《中国古代房室养生集要》(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3年)5-6。)在对身体的重视和强调方面,密宗显然借鉴并吸收了中国古代养生学方面的说法,但密宗本身是很复杂的,不能将密宗的性仪规与性实践等同于中国的房事养生学。再者,密宗毕竟是一种宗教,其性力体验与宗教苦行的体验在获得非我、忘我、无我、意识控制等方面是基本一致的,因此,苦行和性欲并不截然对立,而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苦行是通过禁欲的方式来集聚自身的能量,而密宗则通过纵欲的方式来激活自身存在的热量;前者是“灵”的修行,后者是“身”的修行。所以,在密宗看来,身体最为神圣。
伴随着身体的神圣化,性事也被看得极其崇高而神圣,性力本身就象原始的宇宙创造力一样神圣而永恒。这种神圣化了的性事的最典型特征,在于它将世俗的“爱”和“情”完全彻底地剥离出去了。在密宗经典和密宗实践中,“爱”没有立锥之地。密宗特别强调对各种关系形式包括心理和社会意义上的爱的拒绝。性交仪式中的女性代表着纯粹的性,是女性原则或性力的体现,而不代表着她是一个女人。人类感情意义上的爱对于修行密宗的人来说是完全不能相容的,它将性行为从个人和社会中孤立出来。不带情感、不带功利的世俗的性行为是最为神圣的。当然,也可以说,密宗对世俗之“爱”的拒绝,意味着它追求的超越世俗的圣爱,但这并不是柏拉图式的理想之爱或是西方宗教中的圣爱,相反,它是将宗教意义上的圣爱拉回到现实之中并使之世俗化了。这对于印度的宗教哲学、艺术、文学等等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印度著名的梵语诗人伐致呵利说,在这个无常的世界上存在着二种生活方式:其一,献身于宗教,因为其中充溢着真理和智慧,从而使人能够体验到无穷的乐趣;其二,与风情万般的性感女子一起享受生活显然也是美妙无穷的体验。这二种生活方式并不矛盾,在伐致呵利的心目中,当圣人拒绝年青美貌的女子时,他实际上是自欺欺人,因为他进行宗教苦修的目的不过在于获得天堂美女的青睐。他还通过文字游戏以极其世俗的方式嘲弄了追求宗教意义上的解脱之人:女人的乳房是珍珠镶嵌的地方,这里的“珍珠”(Mukta)一词在梵语中也指“(宗教上)获得解脱之人”,此可谓妙笔生花的双关语,伐致呵利在此不仅颇具风情地夸饰了女人的乳头,而且还轻松调侃了宗教圣人,原来是坐在女人乳房上享受的小玩意儿。(注:See Lee Siegel, Sacred and profane dimensions of love in Indian traditions as Exemplified in the Gitagovlnda of Jayadev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19.还可参阅《伐致呵利三百咏》第139首,金克木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62。)既赞美女人又嘲弄宗教的双关诗意是梵语宫廷艳情诗的一个典型特征。
描写艳情是印度古代文学的一个典型特征,艳情诗主要反映印度古代上层社会的生活情调。一般来说,梵语宫廷艳情诗是非个性化的,语言极其精致雕琢,因袭于约定俗成的传统,致力于语言与技巧的游戏,梵语诗学从这些诗歌的创作中总结出一套系统的理论,并对各种技巧详加分类,反过来,诗人又严格遵守这些理论,逐渐形成高度风格化的、精美的文学样式。梵语文学的主要功能在于愉娱,它对于享乐尤其是性爱享乐方面的感情的描写较为细腻。
再一种情况就是,艳情诗人借助于对神灵性爱游戏的细致入微的描写,从而将宗教意义上的圣爱世俗化,世俗意义上的性爱宗教化,消弥世俗与宗教之间的界限。黑天大神与女友罗陀以及牧区女子之间的性爱故事不仅是印度的宗教典籍和文学作品热衷的题材,而且在民间故事中也极为风行。对大神的虔敬不仅是一种宗教奉献,而且演变成了热烈、迷狂的性爱。毗湿奴大神化身为魅力无穷的风流少年,成为千万女子日夜渴望与之性爱、与之偷情的对象。偷梁换柱,借助于黑天大神,人类生活中日常而暂时的性爱变成了永恒的存在。欲望也不再是解脱道路上的障碍,相反,它成了获得解脱的有效途径:现实生活中的欲望本身并没有发生什么质的变化,只要热爱黑天大神,就可以尽情地满足欲望。每一个男人都是黑天的化身,每一个女人都是渴望着黑天的罗陀。只要听到了黑天吹奏的笛声,每一个女人都会来到黑天身边与他尽情地狂欢。
当印度古典诗学家试图寻找一个词语来概括艺术的本质时,他们选择的词语是“味”(“rasa”)。制作美味佳肴的关键在于调味品,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的创作关键在于创造出情味。在《梨俱吠陀》中,“味”指的是液体,尤其是植物的汁液,是各种事物的本质或者说是元气。但是到了密宗那里,“味”则具体化为人身体中的精液和血液,这样,“味”既是性爱的感情享受,又是性爱的生理体验本身。春天不仅是诗人笔下恋人们的季节,它更是苦行者的大好季节,因为在这个季节里,苦行僧们也在化精提气:通过打坐和呼吸的控制使他的精气在他的全身运行起来。宗教上“味”的说法来自美学上的“味”论。从宗教体验的角度看,“味”是一种狂喜的境界,它是世欲意义上的男欢女爱与对黑天大神的圣爱之间的结合,在印度人的想象之中,神与天国就是最直接和最无拘束的欢乐:花环、蔓藤、美女以及美女身上的珠光宝气。
《抱朴子》对俗(九)
?《抱朴子》是东晋医药学家、道教先贤葛洪所著。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抱朴,是道教术语,见于《道德经》“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抱朴子》今存“内篇”20篇,属道家;“外篇”50篇,属儒家。八仙宫仅整理内篇与大家分享学习。
元代画家王蒙所绘《葛稚川移居图》中的葛洪形象
《抱朴子》内篇
对俗
或问曰:“为道者当先立功德,审然否?”
抱朴子答曰:“有之。按玉钤经中篇云,立功为上,除过次之。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
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行恶事大者,司命夺纪,小过夺算,随所犯轻重,故所夺有多少也。
凡人之受命得寿,自有本数,数本多者,则纪算难尽而迟死,若所禀本少,而所犯者多,则纪算速尽而早死。又云,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复中行一恶,则尽失前善,乃当复更起善数耳。
故善不在大,恶不在小也。虽不作恶事,而口及所行之事,及责求布施之报,便复失此一事之善,但不尽失耳。
又云,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若不服仙药,并行好事,虽未便得仙,亦可无卒死之祸矣。吾更疑彭祖之辈,善功未足,故不能升天耳。”
■《抱朴子》内篇“对俗卷三”到此结束,明天起将继续学习下一个篇章,“金丹卷四”。
【解释】
有人问道:“追求仙道的人应当首先建立功德,确实是这样吗?”
抱朴子回答说:“有这种说法。《玉钤经中篇》说:“建立功德为最好,免除过错的就次一等了。修炼道术的人认为救人于危难,使人避免灾祸,医治人们的疾病,使他们不白白地死去,这是最好的功德。
追求仙道的人,首先应当把忠孝、和顺、仁信作为根本。如果不去修养品德行为,只是一味地去学习方术,那是不可能长生不老的。做了重大的邪恶之事,司命神就会扣除他一纪的寿命,干了小点的坏事,就会扣除他一算的寿命,根据所犯过错的轻重,所扣除的寿命也就有多有少。
世俗之人接受命运、获得寿命,本来有一定的数量。数量本来就多的,纪算就较难扣完,要很晚才会死亡,如果所禀受的数量本来就很少,而所犯的过错又多,那么纪算就会迅速扣尽而很早就会死掉。还说:“人如果想当地仙,就应该做三百件好事;想做天仙,就应该做一千二百件好事。如果做了千一百九十九件好事,却突然在其间干了一件坏事,那么就会完全丧失从前所有的好事,又应该重新开始计算做好事的数量。
因此做好事不在于其大,做坏事不在于其小。虽然不干坏事,却夸耀自己所千的好事,以及索要干好事的回报,就会丧失这一次好事的善果,只是不会完全丧失而已。
还说:“积累善事没有达到标准,即使是服食仙药,也没有用处。如果不服食仙药,只是不断地干好事,虽然不会马上成仙,但也可以免去突然死亡的灾难。我甚至怀疑彭祖这些人,就是由于善良的功德还没有达到标准,所以才不能升入天庭的吧。”
声明: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本站部分文字与图片资源来自于网络,转载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立即通知我们(管理员邮箱:15053971836@139.com),情况属实,我们会第一时间予以删除,并同时向您表示歉意,谢谢!




在线学习.png)


.png)
在线学习.png)
在线学习.png)